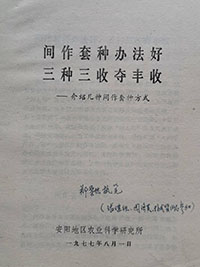1977年,我从濮阳农村回农科所,当时形势是全国上下批“四人帮”,一方面强调要 “按既定方针办”,另一面强调“两个凡是”,对于 “文化大革命”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,当时的党中央不承认发动“文革”是错误的,没有承担责任为下级解套,“山雨欲来风满搂”,报纸一篇接一篇发文章把“造反派”与四人帮划上等号,似乎非要在每个基层单位都抓出 “小四人帮”来不可。这种本末颠倒的作法又一次引起群众间派别之争,派别裂痕加大,原来两派争着当“造反派”,这时却避而恐不及,谁也不承认是“造反派”了。种种迹象表明,自已将在劫难逃。
当时我名义上仍是革委会副主任,上级也未明确宣布靠边站,但凡有关政治运动之事,已不让我参加,只参加革委会部分工作会议。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自已也只能管管科研和生产,昔日之权威荡然无存,工作抓不动,挑子也撂不掉,遇到困难,曾多次掉过眼泪。这种好象“看守内阁”阁员的尴尬处境,持续了几个月,有谁能解个中味呢?此间,和张继祖、周济英、杨式贤执笔编写了《间作套种办法好,三种三收夺丰收》小册子,印刷数千册在各县散发。大力推广麦垅套种玉米技术,对全区玉米增产影响巨大。
九月和十月干旱无雨,影响到秋播,地委组织抗旱工作队,我被派到长垣县抓抗旱种麦,当时工作组长是原地区农科所所长李自如(已到地区科委任主任),我跟着他到各乡去督促抗旱。私下他劝我说:“小郑,别有顾虑,我佩服你在文革中对待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态度,敢讲真话,心地善良终有好报!”
这年岁末,农科所四十多人进了安阳第二招待所,参加安阳地委举办的“揭批查学习班”,当然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,有人是动力,有人是挨批对象,我将是后者。
进学习班挨批判是顺理成章的事,早有思想淮备,但我知道,自己虽在所领导岗位三年,但实际主持工作只有短短几个月,纵有千错万错也罪不当诛。上纲上线批判,大会小会批斗,我的所谓“罪状”主要有两条:一是包庇坏人,认敌为友(指我仗义执言,说文革中定的 “反革命”是朋友不是敌人。);二是攻击党中央(指“评纪登奎同志讲话”,因为纪登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,而大字报内容全部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)。当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会以言获罪了,而在中国也有“言者无罪”之古训,但实际上历朝历代仍然以言治罪,甚至有人把它当成 “国粹”!
批判归批判,难以心悦诚服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人们私下偷偷在议论:真正需要检讨和反思的不是某人某派,而是中央长期的左倾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!只有实事求是,放眼大的环境看问题,才不会重蹈覆辙。
1978年春节快到了,人们忙着操持办年货,风声大雨点小,即使按当时的法典,也找不到任何给我定罪的依据。心知肚明,批判的目的是找点理由免除职务而已!
经过无数次批判和检讨,“副县级”的乌纱帽终于摘掉了,它使我饱尝高处不胜寒的滋味。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高的官衔,戴上时并未特别快活,摘掉时也没有特别诅丧。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小农业技术员而己。
“文革”十年噩梦总算结束了,拂平心灵创伤需要时日,让人们彻底从梦中醒来,打破思想禁锢,决非三年五载之事。
几年后,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结论,今后不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,不幸的是,我正赶上这最后一次。